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高林的专访。更多系列文章会陆续推出。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随着学术体制的强化,专业历史写作与通俗历史写作分道扬镳,通俗历史写作则成为大众与历史专业之间的桥梁。但随着媒介变迁,通俗历史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谈论有趣的历史,或许将成为一种潮流。

高林,曾用笔名高凌、克罗采和春天。青年历史学者。
1
“美好年代”与通俗历史写作
在历史学术界,一些青年历史学人如新星般冉冉升起;但在学院外,大众或许并未听过他们的名字。由于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许多普通读者或许不会直接阅读专业作品。这就造成了专业历史写作与通俗历史写作之间的隔阂。但在历史上,专业历史学作和通俗历史写作之间并不一直存在隔阂。历史学家许纪霖就曾经谈到,实际上从“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存在着为大众写史的传统。那时的历史大家,所写的文字都流畅通俗,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这些作品不是写给专家看的,而带有启蒙公众的作用。
但随着学科专业化的强化,以及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入,专业历史写作和通俗历史写作开始分道扬镳。专业历史写作需要符合学术规范,其写作对象是同行。因此,专业历史写作里的“学术黑话”越来越多。在学术界外,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也催生出一大批通俗历史作家。许多通俗历史作家也受益于新世纪媒介的变革,比如红极一时的央视节目《百家讲坛》就曾带火过许多颇有影响力的通俗历史作家。
在《百家讲坛》红火的年代里,通俗历史作家承担起了连接专业与大众的作用:优秀的通俗历史作品意味着把专业的历史知识,以通俗易懂,尤其是以讲历史故事的方式普及给大众听。在社交网络时代到来后,新的媒介特性改写了通俗历史的创作方式,也为新一代通俗历史作家的诞生打开了大门。专注19世纪欧洲“美好年代”历史的公号“青年维也纳”的创始人高林就是这样一位代表。在“青年维也纳”里,读者可以看到欧洲“美好年代”里不同的碎片(这正是互联网时代的特性)——从文学音乐,到社会政治——其共同点就是有趣。对于高林来说,历史是一种爱好,他想将他感受历史的乐趣,在互联网上分享给他人。谈论有趣的历史,而不是像讲故事般地讲述历史,同样都是历史写作的一部分——而这种历史写作方式在近几十年间已经衰落了。
欧洲“美好年代”时期法国艺术家尤金·加林·拉卢所绘的巴黎街景。欧洲“美好年代”一般指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这一段历史时期。此时的欧洲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美好年代”是后人对此一时代的回顾。
2
对话高林
新京报:“青年维也纳”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高林:《聚书的乐趣》的作者爱德华·纽顿说,“一切不能方便地向别人推荐的爱好都是难以持久的”。被他拿来当反面教材的爱好是集邮。我每次看到我爸的集邮册,就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
向别人推荐历史,比向别人推荐收集珍本图书要方便。因为我们只需要说话,连图书目录都不需要展示。“青年维也纳”其实就我们发展相同爱好的网络平台,我们在上面进行文字化的聊天或布道。在这个群体中,没有谁是专业的历史学者。对我们来说,历史仅是个人爱好。但你也懂的,爱好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下线。历史很有趣,我们想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青年维也纳”的本源。
新京报:历史学领域内的内容如此之多,你为何会选择十九世纪的“美好年代”作为自己的写作和研究方向?如何看待你所书写的“美好年代”与当代之间的联系?
高林:“美好年代”的魅力体现在两点上。首先,“美好年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夹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时代。生活在“美好年代”的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年代只是一段插曲。他们看着十九世纪的大幕落下,二十世纪的大幕徐徐拉开,并对此感到既激动又不安。其实,这种矛盾的心态和如今这个时代里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
在这一点上,“美好年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为我们的矛盾心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也是“美好年代”另一点的魅力所在。“美好年代”是一个事与愿违的时代。人们盼望着二十世纪的到来,但二十世纪的到来却把他们对二十世纪的所有愿望都一扫而空。
我们作为出生于二十世纪末的一代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美好年代”里的人曾经期待的二十世纪,其实是一个异常疯狂和黑暗的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好年代”可以成为我们的反面例证。当我们也面对着一个新世纪徐徐拉开大幕的时候,我们最正确的选择是过好眼前的每一天。这就是“美好年代”作为镜子的一面。
新京报:在“青年维也纳”里,大家谈社会、政治、文学、音乐、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几乎无所不谈。公号文章语言风格风趣幽默。这样能让知识更好地被读者所吸收,但这或许也产生知识碎片化的问题。我看有评论说,你的《皇帝圆舞曲》有点知乎问答的味道。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评论的?为何会选择比较碎片化的随笔写作方式,而不是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历史写作?
#p#分页标题#e#高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研究领域里,写作者好像只剩下了两件事可以干——一个是学术研究,另一个是科普。学术研究要求写作者按照学术范式来写作,科普则要求写作者首先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基础水平,然后再把历史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讲出来。
但是,历史既不是我所追求的学术事业,也不是我要向任何人进行科普或者上课的学科。对我来说,历史只是一种爱好、消遣和乐趣。上课是没有乐趣可言的,听课也没有乐趣可言。
把乐趣传达给其他人的前提,并不包括要把历史的各个方面,以非常系统的、事无巨细的方式来讲历史。如果读者真的对历史产生了兴趣,读者应该自己去了解这些事情。我要做的是,跟大家讲历史中我认为有趣的那部分,或不该被人忽略的那部分。我这种历史写作,面向的是有历史基础的读者。谈论有趣的历史,而不是像讲故事般地讲述历史,同样都是历史写作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历史领域本身的专业化和社会自身的发展,这种历史写作在近几十年里越来越衰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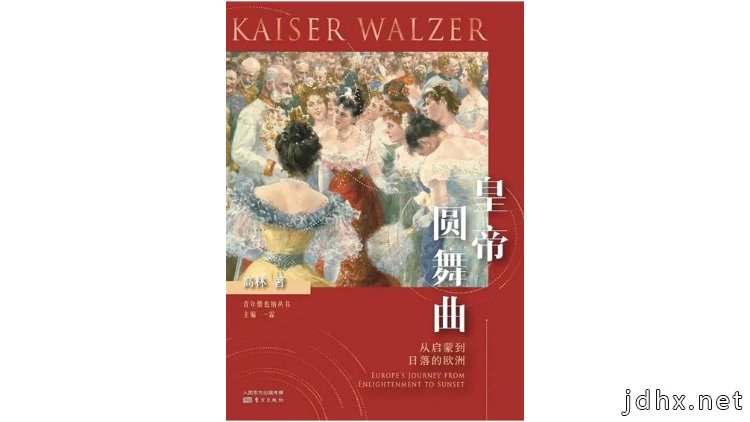
《皇帝圆舞曲:从启蒙到日落的欧洲》,高林 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3月
新京报:有人说专业的、依附于学院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历史学者,其写作越来越专业化,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本该面向公众的一面。如今通俗史学非常流行,但其中又有大量良莠不齐的东西。你心目中好的历史写作是怎么样的?
高林:现在,历史是一门科学。但在古代,历史是一门艺术。历史和诗、戏剧和小说曾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现在历史成了一门科学,跟艺术分道扬镳了。历史科学化的结果是,专业历史写作者和通俗历史写作者都不在乎自身的文学性。没人关心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看,只关心自己写的东西正不正确。历史科普就是在正确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以通俗化的讲述方式讲给大众听。
但是,我个人更希望存在着一种比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在历史中,我们不单想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也想知道那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里的其他人,都是怎么度过他们这一生的。
如果历史写作者能客观地把一个历史人物自己的愿望和所处时代里不同阶层的人的愿望都表达出来,并告诉读者,这个历史人物掌握着什么样的资源和能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在哪些情况下这个人物改变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个人物又被时代所战胜。那么,历史写作者在客观上就展现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和心灵。这其实和小说家在虚空的场景里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新京报:作为一个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你认为你跟学院里的历史研究者在视角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高林:作为一个非学院派的作者,我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概括起来就是《虎口脱险》里指挥家对德国军官说的那两句话:“这个好吃!这个能吃!”历史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它陪伴我度过了很多平静而美好的时光。我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历史。我既不能也不想从事学术写作(当然首先是不能),我又不打算给任何人讲历史故事,那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谈谈我所感受到的历史。
看到历史作为生活的一面,同时也看到生活作为历史的一面,这是我感受历史的最大乐趣之一。如果秉承这种心态去看待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物其实是由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扮演的,只不过有些人物站在了聚光灯底下,让我们误以为他有三头六臂而已。
- 广西中烟柳州卷烟厂练好四项基本功提升新闻写作水平
- 用30节唐诗写作课,教孩子写高分作文!
- 兴中学校举办新闻写作培训会
- 公益性岗位公共基础知识:公文写作主观题之通告的写作技巧
- 小记者新闻写作班昨日开课(图)
- 就如何增强新闻工作者“四力”省新闻道德委召开专题评议会
- 全国著名文学刊物编辑在宁点评:青年写作要跳出新闻
- 基于理论层面对受众调查的理解与反思
- 台湾图书馆举办朗读夜活动
- 南京会写商业计划书本市公司在哪?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德迅网 » 把历史写作,作为一种消遣|专访高林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互联网分享,不代表本网的观点和立场。

 表达侨界心声,悉尼华星艺术团创作MV《把
表达侨界心声,悉尼华星艺术团创作MV《把 【配乐诗朗诵】白衣天使礼赞
【配乐诗朗诵】白衣天使礼赞 法媒:美国“悬疑小说女王”辞世 七岁就爱
法媒:美国“悬疑小说女王”辞世 七岁就爱